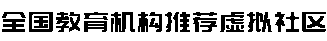该文是《宏大理想的捍卫者》续篇
从一个故事讲起。几年前我跟一位老友吃早茶,现场有一位行业中的新人加入了我们,在旁边静静地旁听。老友问我一个私立教育中绕不开的问题:教育对于消弭不平等的神圣使命与商业化教育中逐利属性间是否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我心下开朗,跟他说了三个词组:先验与综合的定言令式、无知之幕后之后的差异性原则、间接功利主义。他沉思片刻,抚掌大笑曰,妙哉妙哉——当积极自由在形而上层面上被设置了道德底线后,私立教育就可以搭载自由市场规律的巨轮发挥其最大功效了!
而不久前,那位在场的当年的行业新人才刚刚告诉我那次短暂谈话中他的巨大的沮丧感:在他的视角中,只看到了两个疯癫的哲学爱好者故弄玄虚地卖弄着玄而又玄的华丽词汇,他自己却无法与我们共情。他这样一说,我仿佛依稀记得小伙子当年困惑而尴尬的笑容与若有所思的神情。
于是,这让我意识到了“知识的诅咒”如魅影般的存在。
在解释“知识的诅咒”是什么之前,我先给各位描述一下——如果想把关于教育的这个问题对话完成,那个小伙子需要透彻地理解下面的知识:
在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困境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因其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
康德在认识论中发展的先验、后验、分析、综合四个范畴组成的四象限中,道德律所在的位置;
罗尔斯在面对平等与自由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语境下出现此消彼长的困境下,如何用康德的定言令式中的第一式去推导出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位置”。
在上面三个理论作为理解教育与商业命题的第一序列后,他还需要知道第二序列的理论:
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涉猎以下作为第三序列的几个思想作为辅助理解我们的谈话:
可是,如果都拆解到这个层面了,还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话,那么我对我们此生是否有机会能够“沟通”,抱极度悲观的态度。
这就是我想说的“知识的诅咒”,它的狭义概念是这样的:某一领域的专家会习惯于用术语相互交流,从而逐渐丧失了对非专业人士沟通的能力。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教育的使命与商业的逐利本性之间是否存在可协调性”。对于我和创立“孤独的阅读者”以及琢磨文化的战友们来说,这是一个用三个词“定言令式”、“无知之幕”、“间接功利主义”就能轻松解释的简单命题,然而却在实际的沟通中遭遇到难以想象的挫败。
我们目睹了很多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者在用鼠目寸光的方式来践踏康德原则;
我们面对很多大环境下掌握着权力的巨婴们原始落后的非黑即白式的思考模式;
在孤阅学习的成员们很多还要去应付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嘲讽与不解——“学那些顶饭吃么”、“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
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谬论其实都可以这样用两三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词语瞬间击破。我们的沟通的效率提高了恐怖的千倍甚至万倍量级。
我做一个类比——人类的知识就像珍珠项链一样:
知识的诅咒,如恶鬼般,侵蚀着我的耐心与勇气。它是造成我对教育事业忧心忡忡的老巢,但它也是不断挑衅我、激起我狂怒的战斗意志的源泉。
知识的诅咒,一个不起眼,但穷凶极恶的词眼,其广义概念却令人的更加震恐——当交流双方知识结构不对称时:
再通俗地讲,如果我们把人类按照知识储备程度自上而下排列,那么在这个上下序列中,我们很有可能永远被禁锢在某一个阶层,我们既无法理解下层为何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我知道那么你也应该知道;也无法理解上层为何关心那些无用的道理——我不知道等于不存在。
知识的诅咒让一个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发生了扭曲。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时间是几十年的生命历程,而我们却读着二手的史书陟罚臧否;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空间不过是几个村庄县市,而我们却读着新闻时政挥斥方遒。能被史书记载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某一个时代最不寻常的事件;能被新闻播报的东西大多是罕见的新鲜玩意。这些根本没有办法的还原真实的时空,那真正的时代精神,往往被排斥于我们的注意力之外。
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不熟悉不等于不重要。不关注不意味不值得。
然而正在我将这些对于知识的诅咒的描述一字字敲出来的时候,我本质上正在创造着又一个知识的诅咒——能够看懂的人往往早已经打破了知识的诅咒,不再需要这样一篇文章;而真正需要打破知识诅咒的人却不会看懂。
这恐怕是令我最为忧虑的事情。
因为我在批判他人无知、被知识诅咒之后,我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自己是否也同样被知识诅咒。
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命题。
我们的国度,就像很多其他的巨型社会一样,由一堵一堵隐形的墙将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隔得壁垒森严。我们这样一小撮极其幸运的人如果没有主动踏出这个圈子,便会认为自身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也会认为所有的功劳都在自己。我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求学、在北上广深驰骋、在全世界各个华丽的角度用双腿丈量世界时,并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我天朝国民连最基本的通识都不明白,连最简单的英文都学不会,连一些普世的价值都想不清,连最直白的理性思辨都不具备——因为那张无知之幕没有挡住我带着偏见的双眼。那时的我,从未见过穷困潦倒的家庭,从未见过一生都没有走出过村庄不知道外面世界之广大的乡民,从未见过资质平平的小市民,从未体验过的每天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斤斤计较背后的无奈。我没见过也不知道这些,于是我以为他们不存在。
但从象牙塔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更接近于全貌的世界。不仅仅是走遍了中国的山川乡野,也走过了世界其他地方不为人知的角落。我看过流浪的罗姆人的境遇,我自己在墨西哥的佣人是一个穷苦的玛雅人和一个郁郁寡欢的梅斯蒂索人。多年来我都在这些不同国度的隐形巨墙上努力眺望墙那边的世界。那是一副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人沮丧至极,也让我曾经的狂妄自大和洋洋自得烟消云散。
我从事了教育。这就意味着我和我的队员必须予以取舍。我们可以停留在舒适区里,给我们自己圈子里的含着银勺长大的精英子弟传授最高深的知识,收取他们每个人数十万的费用,在自我打造的乌托邦里跟世间的疾苦越来越远。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目光投向那些在那一股细细的改革红利没有覆盖到的最广大的人群,挑战自己耐心的极限,把我们头脑中复杂的知识储备用一个懵懂无知的中下产阶级少年也能听懂的话讲出来,收取一笔仅够项目存活下来的费用,牺牲掉英美大学课程中必不可少的个性化十足的“研讨会”,牺牲掉对于精英们算是标配的每日数百页英文的阅读量,牺牲掉我们曾经以为的教育理想国的一切高标准的细节。
我们选择了后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那个极难模式的后者。因为我觉得,像我一样的这群时代的幸运儿,手里攥着大把大把的机遇,身负着祖辈的名望、强大的方法论、深刻的家学渊源,再多的教育项目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而市面上廉价的网课众多,内容的传授都是令人厌恶的投机取巧、蝇营狗苟,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在各种三流五流的大学颟顸度日虚度年华。我们不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这些年轻人的青春,拱手让给一群不知所云的投机钻营者。因为他们既不是宏大理想的捍卫者,也不是宏大理想的恶敌。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他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无知的恐惧和时代大潮造成的慌乱中的一种自保。
然而这并不是说孤阅就是什么完美无瑕的美玉,我也没有任何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企图。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与头顶的星空告诉我:
不作恶。
仅此而已。
宏大理想的恶敌,是知识的诅咒。
它的险恶,在于宏大理想的捍卫者在挑战知识的诅咒时,同时就在被知识诅咒着。
这将是一场鏖战。